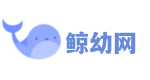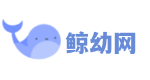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被判死刑,最后陈述时说:“分手的时候到了,我去死,你们去活,谁的去路好,唯有神知道。”(柏拉图《申辩篇》)孔夫子和苏格拉底在各自的国度堪称圣人,但对死亡都表示不了解。

东汉向子平(名长)隐居不仕,喜欢研读《老子》、《易经》。一次读《易》至损、益二卦,喟然而叹:“吾已知富不如贫,贵不如贱,但未知死何如生耳。”(《后汉书》)他后来弃家游五岳名山,不知所终,也不知是否找到了答案。
法国作家拉伯雷在《最后的话》中也说:“我去寻找一个尚属疑问的伟大的东西。”找到也好,找不到也罢,都无法告诉我们了。
世界上许多知识都可以通过经验获得,但死亡的经验却谁都没有;许多知识都可以验证,而关于死亡的知识却无法验证,至少是无法亲身验证。人们虽然可以间接地认识死亡,通过别人的死亡来认识死亡,却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死后的情况:究竟是人死如灯灭,还是灵魂离开身体继续存在?倘若灵魂不灭,那么,彼岸世界比此岸世界怎么样?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人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,对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总是不大相信。

南宋叶衡罢相还乡,每日与门客饮酒消遣。一日忽忽不乐,对门客说:“某(我)且死,所恨未知死后佳否耳。”一门客说:“佳甚!”叶惊问:“何以知之?”回答说:“使死而不佳,死者皆逃归矣。一死不反,是以知其佳也。”(岳珂《桯史》)这不过是帮闲者的一个噱头,但死者一去不返却是事实。正因为一去不返,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经验,死亡于是被视为不可知。
除非死而复生的人,或许对死亡有发言权。历代笔记中多有再生之类的记载,但率多荒诞不经,不足为训。倒是弥留之际乍死还生,庶几可以谈点感受。北宋僧人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载,尹洙(字师鲁)被贬官过邓州,手书(亲笔信)与范仲淹诀别。范仲淹得书从南阳赶来,尹洙已沐浴更衣,少顷端坐而逝。范仲淹恸哭失声,尹洙大概听到了,忽然又活过来,抬起头说:“死生常理也,何(何以)文正(范仲淹谥号,生时不应称此)不达此。”问他后事,尹洙说:“此在公耳。”与范仲淹相揖而逝。少顷再次活过来,举手对范仲淹说:“亦无鬼,亦无恐怖。”说完才真正与世长辞。尹洙在最后死去前,已死过两次,“亦无鬼,亦无恐怖”就是他对死亡的切身感受。
其实,真正了解死亡,并不需要亲历死亡;即便可以经历死亡,又岂能真正懂得死亡?这就像人们虽然生活过,却未必真正懂得生活。孔夫子是生活过的人,而且比子路多吃许多咸盐,但他却自认为“未知生”。这不仅是他嫌子路的问题愚蠢,而且是对生命的真谛的确没有标准答案。他毕生都在探求真理(包括生命的真谛),但直到临终都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。从那时到现在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,人们从未停止这种探索,但对生命的真谛仍然众说纷纭。死亡并不神秘,也并非不可知,正如生存并不神秘,并非不可知。假如死而有灵,死者在彼岸世界想必也会众说不一,正如现实中人们对生命的真谛众说纷纭。其实,人们并不真正需要标准答案,只需了解众说,而又勤于思考,凡事形成自己的看法,也就是孔夫子所谓“不惑”,那么真谛可能就在其中了。
晋代有个名叫苏节的人,其父苏韶死后,灵魂回家达三十多次。一次,苏节问其父:“死何如生?”苏韶(灵魂)回答:“无异。而死者虚,生者实,此其异也。”(《王隐晋书》,据《太平广记》)这当然并非苏韶的回答,而可能是文人墨客的杜撰,所反映的不过是作者的见识,虽然“卑之无甚高论”,却也颇耐人寻味。所谓死生“无异”,大约以为人死后还有另一种生活,与活着时差不多;所谓“死者虚,生者实”,大约以为死者的另一种生活,并不像生者的生活那样实在。现在看来,另一种生活当然并不存在,死后的生活,其实是活人的想象,是活人观念中的生活。正由于此,死才会“无异”于生,因为观念的生活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;也正由于此,死者的虚区别于生者的实,无非就是观念区别于现实。
“死何如生”的问题,是相信灵魂不灭的人们提出的问题,或者至少是对灵魂存在与否不能确定,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提出的问题。苏格拉底相信神的存在,相信彼世的判决将比此世公正,在那里他将受到公正的对待,他还将与众多的哲人为伍,所以他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说:“谁的去路好,唯有神知道”。拉伯雷可能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,是一个怀疑论者,他不相信宗教提供给他的天堂和地狱,所以要“去寻找一个尚属疑问的伟大的东西”。在他临终的时候,出现了很长一阵的沉寂和几乎失去一切意识的症状,也许是要感受一下死亡,就像尹洙弥留之际,只不过他是有意识的,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通过自身的毁灭来寻找一个答案,那答案他可能已经有了,只是没有直接说出来,而是突然张开眼睛,对着死亡放声大笑,说:“拉幕吧,戏演完了!”
本系列已发布文章链接:
解读死生︱死亡与睡眠
解读死生︱死亡与痊愈
解读死生︱举足与落足
【焦加文史随笔】相关文章链接:
太极光阴与蟪蛄春秋
人间岁月长
日长如小年
生命与呼吸
标签: 人死后会投胎吗